第十六章 戛纳的一场闹剧
第十六章 戛纳的一场闹剧
1995年,《代顿协议》 (Dayton Agreement)在巴黎签署,波斯尼亚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米洛舍维奇、图季曼和伊泽特贝戈维奇握手言和。当初,是这三个人带领我们走向了民主,随后让我们卷进战争,现在又是他们把我们推向和平。很多年前,安德里奇写过一篇论文,文章里面明确写到:巴尔干地区的冲突永远解决不了横亘在多个民族之间的问题,反而会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迫使我们用更多新的战争来解决。我很清楚,刚刚结束的战争恰好印证了安德里奇那篇年代久远的论文。
同年,《地下》在戛纳得胜,我收获了第二个金棕榈奖。这次与1985年《爸爸出差时》得奖不同。想当年,如果我知道他们会因为那部电影把我标榜为反共产主义代表,我是绝对不会拍的。1985年颁金棕榈奖给我的那些人,如今当他们看见我已经变成了怎样的“政治动物”时,心里肯定会生出不同的感受,我想他们完全可能让我把原来的那个奖杯给他们还回去。
《地下》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这一次,让我成为熠熠生辉之星的,是电影本身的美感。曾悬挂在泽尼察上方煤烟色天空中的那颗星,继续着它的行程——从威尼斯到戛纳,到柏林,到其他地方……其实我更觉得,《地下》在奢华堂皇的电影宫里放映结束后,随之而来的安逸与欢愉,才让评审团成员们对我有了好感。一个影评人甚至说我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直系后裔。他肯定是有些夸张了,不过当今的专家们能研究出点儿什么结果,谁又能说得准呢。我本想低调一点儿,可一句蠢话反而有了自吹自擂之嫌。
“其实,我是狄俄尼索斯其父亲之子。”我用法语回答他。
那个影评人看着我,有些发愣。
“所以,你要不是狄俄尼索斯的话,就是狄俄尼索斯的兄弟了?”他问。
“不是,我是狄俄尼索斯其父亲之子。”我固执己见。
他盯着我,一脸困惑,最后他笑了。
“即便这说不通,听起来倒是不错,我把这个名号给你了!”
“好吧,我希望你现在明白了。”
后来,我花费很长时间绞尽脑汁想理清这个想法,这明显是喝了啤酒昏昏欲睡造成的结果。一杯鸡尾酒能让脑容量翻倍,可同时也让人丢了领会能力。然而要想克服电影节带来的巨大压力,酒精是唯一办法。最后,我停止了对这句蠢话不着边际的推论,而且我自己也站到了那位法国评论人的一边:这听起来倒是不错。
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决定把金棕榈奖再次颁给我,我把这归因于他们深深的怀旧之情——这世上再没有了布努埃尔,没有了费里尼,没有了贝托鲁奇,他们分外惋惜。而我,在这个20世纪的末尾,我唤醒了他们对过去的回忆。今天,看得很清楚,影响我命运的有两个外部因素。但我不会分析内部原因,因为那可能会让我到达某个地方,到达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而且那将会是个不太“fancy”的去处。至于那些隐秘的动机,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是终极行家,然而已经没人愿意听谁谈论这些了。灵魂的深度——这个与人类存在紧密相连的本质问题——现如今还有谁对此感兴趣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就算是在俄国,也并没有很受欢迎。在那里,人们更多地是为托尔斯泰和普希金而疯狂。《时代周刊》的文学评论家们也是一样。他们把托尔斯泰摆到了第一的位置,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呢,全球一百位最伟大的作家中都没有他的名字!《时代周刊》和俄国人这般沆瀣一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父亲对我说过:“如果你成不了费里尼,至少也要成为德·西卡。”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很显然我已经满足了父亲这个不太谦逊的心愿。这个愿望就这样被实现了,尽管我真正的目标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不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脸红。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要求。然而现在看来,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对我在电影事业上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电影中,从母亲身上继承而来的——曾让卡塔戈沃鲁西奇路9A里的居民在电梯里照得见灯光的那股坚强的个性,一路支撑着我。好像桑卡不让邻居们偷走灯泡的固执中早已写下了我的命运。
我的照片出现在了《时代周刊》上,与之一同出现的还有一篇理查德·科利斯(Richard Corlis)的文章——一篇并非真正叙述《地下》大获成功的文章。14年前,在威尼斯,《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也引起了与此相同的反响。1981年9月,同样是这本杂志,在电影节评论专栏里,有人这样写道:“获得大奖的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电影,这电影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人物拍的……”那时候,谈到那部电影,人们总是惜字如金。这是一个殖民主义性质的玩笑,没有什么恶意,可殖民主义就是殖民主义。这就是那个年代所谓的“cool culture”。在这十几年里,有些事情已然发生了改变。到了1995年,这一次在戛纳,拍这部电影的已经是个“什么人物”了——尽管一些人仍在否认,可只要看看各色评论,就不难发现这一点。而我,就正是那“一些人”中的一个。有许多评论家断言,在这十几年里我已经成了“人物”,我偶尔会心生怀疑,不过幸好不是经常。
《地下》获奖之后,各大报纸上哪里还有地方可以写写关于这部电影本身的内容啊,因为在马丁内斯酒店门前的沙滩上,爆发了一场大混战,相比于电影本身,这个主题可要有趣的多。看吧,为庆祝获得大奖,大导演参加群殴!还有人故意拿我的“野蛮”个性做起了文章。“如果你用拳头或是不会伤人的物件儿打架,那人们自然会觉得你是野蛮的山野村夫”,印度一句古老的谚语就是这么说的。可当你投下成吨的炸弹,再加上原子弹,那你就是“在执行文明的使命”。1995年的那天晚上,我就是在执行狄俄尼索斯的使命。《地下》从荧幕上、从得到金棕榈奖的大厅里,转移到了马丁内斯酒店门前的沙滩上。
电影宫里,我的希腊同行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风风火火地出现了。他深信,那天晚上,自己的名字会闪耀在胜者的行列中。他就是一枝自恋的水仙。我透过摄像机看见了他,他正在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登上覆着红毯的台阶。他、他的演员们,还有他剧组里的成员,大家手拉着手,煞有介事地朝金棕榈奖杯走去,就像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乡下舞者。没能拿到“大奖”,他不太能接受。
“我还为金棕榈奖专门准备了一段演讲,可现在我全都忘了……”典礼上这位希腊导演说道。
两天前,这个愤世嫉俗的人在《先驱论坛报》的专栏里发声:“为什么在这儿,在戛纳,大家这么喜欢那个库斯图里卡?他的那些电影里就只有喝酒、吃饭和跳舞,这是什么电影艺术啊?深刻的思想藏在哪儿呢,他有思考过吗?”这个希腊人咄咄逼人。在他的电影里,他极力表现得很“cool” ;而在现实中,他做什么都像个海德堡人一样,没有生他养他的雅典郊区的印记。他拍电影,更多是想表达自己对德国哲学的热爱,而不是为了让人类振奋精神。就好像他根本不知道,很久以来,好莱坞的人早已明白——电影大于生活。
经历许多隆重的仪式之后,我女儿杜尼娅也多了几分成熟。记者招待会之后我还要跟摄影师们见面,在这个空档,她指着安哲罗普洛斯:
“埃米尔,你要当心那个家伙!”她悄声对我说,“要是他逮着机会,肯定会偷走你的棕榈奖杯!奖杯还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我看见他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我本来一直把奖杯紧紧握在手里,可听完女儿的警告,我一手搭在希腊导演的肩上,把他带到一边。听到我直截了当对他说这些话时,他显得局促不安:
“西奥,你要是想在这里转上一两遭,我可以把金棕榈借给你,不过有个条件,完事儿之后你得把我的玩意儿立马还我!”
他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流露出一股仇恨,没有丝毫伪装;除此之外还有一丝遗憾,因为他不能一拳打断我的鼻梁。不过说到底,他有这样的反应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有前来为狄俄尼索斯庆祝的人,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与《地下》里的人物有着相似之处。而这一切都是安哲罗普洛斯所恨的,他希望自己才是能在戛纳电影节得胜的那个。
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出现在了马丁内斯的沙滩上,她身穿一条十分漂亮的红色连衣裙,就像是从《一千零一夜》里走出来的公主。她的面容吸引了狄俄尼索斯所有宾客的目光。一张写满无辜的脸颊,流露出一种渴望男性保护的强烈欲望。她在酒店门前的沙滩上游荡,手握一只香槟杯。夜更深些的时候,她跟着萨利耶维奇管弦乐队的东方韵律跳起舞来。很快,她就醉了。她身上愈发有狄俄尼索斯的风范:深夜,一个女人,在舞步和酒精的作用下,一副鬼魂附身的状态,准备好奋不顾身投入到冒险与激情当中。亿万富翁的信使——给我带来消息说有钱资助《地下》的皮埃尔·埃德尔曼,正陪在她身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可这显然不是她的本性,她之所以会烂醉,更多是因为本就敏感脆弱的天性,再加上自己出演的角色没能获奖。埃德尔曼也是那天晚上的赢家。现在,他有个大难题要克服:保护着这样一位很显然并非庸脂俗粉的美人儿,又该如何享受胜利的喜悦呢。皮埃尔也在跳舞,就是很随意地跳,照常扭扭胯而已。当那个女演员躺在沙滩上的时候,他极力追随着她,他在她身边伸展四肢躺下来,望着天上的星星傻笑。
这场景像极了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夜》 (The night),如果没有人打搅,这稍显颓废的镜头本可无止境地继续下去。然而往往在这种时候,注定会出现某个不识趣的家伙——一个从我们山里来的大老粗。
“兄弟,上啊,别磨磨蹭蹭啦,赶紧亲她啊!我了解这种货色,跟她们在一块儿,就应该直接来点儿实际的。”佩贾·博伊嚷嚷道。这是南斯拉夫一个过气了的摇滚明星。
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混进狄俄尼索斯的晚会中来的。我甚至不确定那个著名的女演员是不是注意到自己身边多了个粗俗的家伙。我鄙视那些狄纳里克人[1]的粗鄙行为,他们只知道低下头往女人身上扑,哪怕那些女人跟他们的母亲没什么两样。这个女演员之所以有名气,更多是因为她拍的那些广告,而非她扮演过的角色。在那个时代,演员的荣耀与他们塑造的角色越来越不相干。阿兰·德龙(Alain Delon)参演过数百部没什么价值的电影,可在人们心中,他还是卢奇诺·维斯康蒂的罗科[2]。还好那个时代已经永远成为了过去。她还没出演过真正配得上她的角色,这位女演员的面庞仍然那么纯洁无暇。美丽,却带着幻想破灭的忧伤,让她散发出迷人的魅力。佩贾对自由的理解与她截然不同,他仿佛已经看见自己正跟一个有着天使般面容的女人滚在沙滩上。当他第一千零一次动手撩拨她的时候,她终于注意到了这个男人,而且吓坏了。皮埃尔抓起一只酒杯,照着佩贾的脸扔过去。酒溅到周围人身上,约翰尼的贴身保镖赶忙过来保护这位迷人的宾客。当斯特莱博和乔尔杰明白过来,我们的同胞包括那个可恶的佩贾在内,那晚应该得到我们的保护时,一场战争就此爆发——尽管,一开始,那些保镖只是想保护那个著名的女演员免受佩贾骚扰。一阵拳脚过后,欢庆氛围终于化作一片乌烟瘴气。我眼前这一幕就像是捷克画家约瑟夫·拉达(Joseph Lade)的一幅画,那是一幅描绘酒馆斗殴的画,很是诗意——桌子、椅子、瓶子漫天飞。问这一切是否有必要已经没用了,因为答案当然是没有必要,可事情还是就这么发生了。就像那场战争,终究还是来了,只不过这里没有战争的受益者。说到那位著名女演员,我们当中绝没有任何人会戳她一手指头,但是问斯特莱博和乔尔杰是不是该冲过去跟那些具有骑士风度的守卫者打作一团,也同样没用。因为我们跟那个女演员都是老相识了,如果有谁朝她冲过去,斯特莱博和乔尔杰肯定会像保护自己亲姐妹一样保护她的。
命运之神将狄俄尼索斯在戛纳的晚会导演成了一部你争我夺的丑剧。在这里找不到任何传统戏剧作品的影子。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演员拉扎尔·里斯托夫斯基一记右拳灭了一个家伙,简直跟他在电影《地下》里所做的一模一样。斯特莱博的教父米基·赫尔苏姆,这个刚从波斯尼亚前线赶来的人,专门用他的脑袋撞。不管谁靠近他,他都用脑袋报以猛烈一击,嘴里还一边大喊着:“乌斯塔沙的下流种!”一个巴黎朋友的儿子靠近他,试图让他冷静下来,可米基照样赏给他当头一击,把他也当成了“下流的乌斯塔沙”。然而法国人跟乌斯塔沙半点关系都没有啊。再看看斯特莱博这边,他一个人在跟三个家伙对打,没人知道这几个人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年轻的库斯图里卡有模有样地给了他们一顿狠揍,可当他们三个屁滚尿流逃跑之后,故事一开头的保镖们重又向斯特莱博扑过来。当我还在因为鸡尾酒和啤酒昏昏沉沉的时候,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的马娅急了,她朝那些正把斯特莱博拖向海里的家伙冲过去。马娅顺手抓起一把椅子,一边猛打侵犯斯特莱博的家伙,一边嚷道:
“这是我儿子!别碰他,你们这群蠢货!”
就在这时,楼梯上出现了一群警察。女人们自然希望他们能够介入,以便结束这场殴斗。可她们期待的并没有发生。
“1934年的时候,你们就是这样放任乌斯塔沙杀了我们的国王亚历山大,就在马赛!”他们正要转身,马娅朝他们大喊道。
这个对照让我很是欣喜,被自己的妻子比作一个国王,还是正在打架的时候,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只可惜《时代周刊》的评论员没听见,他在文章里对此只字未提!要是没有这场殴斗,我敢肯定马娅永远也不会把我比作一个国王。说到我,马娅向来很吝惜称赞的言辞,这挺好的。因为我不太能受得了浮夸的称赞,要是有人对我说太多溢美之词,我都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儿了。我更喜欢朴素一点的称赞,比如人家并非刻意说给我听的那种。虽然马娅拿我和国王做对照,但是跟我们的君主比起来,现实情况对我要有利得多——跟他不同的是,我可以选择抵抗。
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凝视着金棕榈奖杯,一脸困惑的神色,“怎么能用这种方式庆祝在戛纳拿了大奖呢?”他的沉思被米基·马诺伊洛维奇打断了,米基一把抄起奖杯塞到衣服里头,想把它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害怕这块金子会被人偷走。在混沌之中,我没发现约翰尼的身影。但我了解他看待周围事物的方式,我敢肯定这烦扰到他了。但因为他是个性情中人,应该不会把这事儿太放在心上。
我在布拉格大学生宿舍的朋友维尔科·费拉克,过去一直关注着我的电影,但他终于厌倦了我那狄俄尼索斯的本性。在跟他的真命天女弗拉尼娅离开马丁内斯酒店门前的沙滩时,他肯定在想,“这个家伙总是惹是生非。”我知道,他看不到我们未来还有什么合作的可能了。如果没有他盯着胶片的专注眼神,我的电影肯定不是观众现在看到的样子。按照他的处事风格和人生目标,这场不合时宜的殴斗是有些太过分了。在拍摄《地下》的时候,他功不可没,但他早已传递给了我一些讯息,预示我们的合作就要走到尽头了。我没什么可以指责他的,也不能说一些破坏我们之间深厚友谊和共同的艺术成就的话。当我看着维尔科搂着他的妻子离开马丁内斯酒店沙滩时,我知道,他也走出了我的生命。
杜尼娅被吓坏了,哭了起来。当我发现马娅为营救斯特莱博正用椅子痛打那些保镖的时候,赶紧跑过去帮忙。事情终于平息下来,只等着狄俄尼索斯给这场晚会画上一个句号了。结局就像传统剧一样中规中矩了。当交战双方都耗尽了精力,或者更准确一点来说,当参与到这场殴斗中的所有人都没了力气——因为这场晚会里没有特别明显的敌对双方,接着关于那几个进场挑起事端的家伙的谣言就传开了,只听见人们谈到秘密组织和其他类似的东西。
我想,如果电影《地下》中那种极富感染力的情感宣泄没有在生活中体现出来,胜者之夜就不算成功。我坚持要明确这一点,因为总有人说我是狄俄尼索斯的兄弟,可“狄俄尼索斯其父亲之子”更合我心意。
一个年轻人从连接沙滩和戛纳滨海大道的台阶上跑下来,狄俄尼索斯的晚会的第二个中场休息结束了。这个年轻人像极了腰间缠着炸弹、冲向受害者的神风突击队员。假设他真的有一颗炸弹,他也没法儿把炸弹引燃。他正跑着,我站到旁边一点,冷静地朝着他的下巴打出一记右勾拳。这下子,这场斗殴真的结束了,因为当这个年轻小伙子的头撞到地面上时,我们所有人都害怕他会丢了性命。又一次,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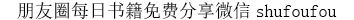
我是不是马上要为今晚犯下的罪行受到惩罚啊?难道我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了吗?
我把这个失去了意识的年轻人抬到一张桌子上。我们往他身上浇水。庆幸的是,他很快睁开了眼,他看着我,眼睛里写满了恐惧,然后……跑了。原来他是马娅介入之前冲向斯特莱博那三个家伙里的一个。
我在戛纳得奖五天后,妈妈在她新海尔采格的公寓里昏了过去。刚从乳腺癌中完全恢复过来——至少按照医生的说法,她的乳腺癌已经治好了。现在她又得了脑瘤。马娅和我搭乘飞机赶过去,当我们到里桑机场的时候,看见桑卡正坐在那儿抽烟。她一看到我,眼泪就涌了出来。
“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让我摊上了,我的埃米尔?”
“桑卡,不管怎么样,你都不会死的!”我极力显得非常诚恳,回答她道。
她接着哭起来,但是凭她拥抱我的方式,我感觉到她信了我的话。我们开车送她去贝尔格莱德的中心医院,约克西莫维奇医生给她开了刀。肿瘤不是恶性的,桑卡很快就恢复了。当内莱·卡拉伊里奇医生来看望她的时候,看到她笑盈盈的模样,医生实在难掩自己的喜悦。
“内莱,你有火吗?”她问他。
“你啊,桑卡,就算是拿把斧子也打不倒你。”内莱断言。能给她点支香烟,他很是高兴。
战争结束后,推翻安德里奇雕像的刽子手跟记者们抱怨,这场战争带给他的只有纠纷。他不仅没有得到奖章,也没有得到“第一战士”的身份。图图姆拉奇把他当成什么事儿都办不成的废物一样丢在一边。他没有得到帮助,安拉没有帮他,美国人也没有帮他。他的房子被洪水一直冲到巴伊纳巴什塔去了。他想让塞尔维亚一直到德金日都被淹的愿望也落了空。他再也不敢回到他位于内祖科的村子,因为塞族共和国的司法机构在他避不到案的情况下,因其毁坏安德里奇的雕像判处他五年强制劳动。萨巴诺维奇声称自己很后悔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还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受了图图姆拉奇的鼓动。为这举动,贝门和加尼奇许诺在珍妮蒂奇齐克米大街上给他一家店铺,就在巴斯卡斯加街区。然而不幸的是,尽管他签了合同,却什么也没得到。最有意思的是,他现在非常坚定地认为,比起那些鼓动他做出这件破坏文物举动的图图姆拉奇,安德里奇是更伟大的波斯尼亚人。“我之所以干了这事儿,是因为他们跟我说这能带领我们走向欧洲?!”在迁居美国之前,萨巴诺维奇这样说。
我想起了那套教育方案,强制要求萨巴诺维奇这个蠢货读完伊沃·安德里奇所有作品的方案。我一直以为应该给所有狂热的粗人开这种方子,这可能会在他们身上起作用,不过在伊泽特贝戈维奇身上就另说了——因为受到一股更大的力量的影响,他转而开始针对我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总统为波斯尼亚准备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早已找美国人当帮手,来了结这场战争,来为他统治的国家起草宪法。因此,在遭受了这么多惨痛的损失之后,他太能够要求美国人给他编造点比保护领地好得多的东西了!
一想到再也不能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城市,我实在没办法心安理得地接受。然而这并不是出于一种负罪感,也不是因为我对萨拉热窝所处的那片陡峭崖壁之间的河谷有多热爱。
除了继战争之后无数的卑鄙言行,说到最后,一些纯粹的个人问题让我感到困扰,其中最让我困扰的就是“咖啡”。
在我的人生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习惯,抑或是一种重要仪式,与我自东方带来的罪恶紧密相连。想要完成这个仪式需要一定的必要条件,而我的故乡成了这世界上唯一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唯一让我中毒上瘾的东西,我把它叫作“共识咖啡”。这种咖啡是要同那些跟你持相同观点的人一起喝,至少他们得是像你一样识得滚石乐队《让我开始》 (Start me up)乐谱的人。讨论能将你唤醒,只要中间不会有人挥舞起不同的观点跟你作对。这杯清晨的咖啡可不是一杯民主的咖啡。这也是为什么我爱共识咖啡!新的一天到来了,不管你在哪儿,如果没有这个咖啡就没法步入正轨。没有这个仪式,这一天就完蛋了,就不存在了。我对共识咖啡的迷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听我这么说,好心肠的人可能会以为我只不过是想竖起一道屏障,为了掩饰我想重回故乡的极度渴望。
“你会梦到萨拉热窝吗?”他可能会这样问我。
“只梦到过一次,在梦里,我走遍了整个萨拉热窝。那真是个噩梦,我蜷缩在一辆没牌照的汽车后座上,车子在我所熟识的街道上行驶着,可路上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然后我就彻底慌了神。”
如果,某天一大早,我奇迹般重回到萨拉热窝,出于好奇,我要去塞塔利斯特喝一杯咖啡。至于这杯咖啡,绝不可能是我之前提到过的共识咖啡。当大家聊的都是人道主义的时候,诸如“我热爱所有的民族,我谁都不恨,好谷子里面总有稗草”等等,那么一切都能在掌控之中。可如果我在喝咖啡的时候,冒险坚持说死亡人数本可以比现在少,那么共识就会翻倒在地,而我的咖啡也难逃同样的命运。因为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应该饶恕:是我们这些塞尔维亚人创造出了这场战争,以及其他所有战争。如果我碰巧还会在欧罗巴酒店喝第二杯咖啡,那么这个共识就必须是:所有塞尔维亚人都应该“被驱逐到俄国去”。在沃伊沃达·斯泰帕街上,加夫里诺·普林西普就是恐怖分子,这根本毋庸置疑。可这样的断言在我这儿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就算加夫里诺不是在维亚纳杀了奥地利大公,而是在这儿,在米利亚查旁边——在奥地利大公统治的国度,还是会有人持有不同的观点,大家依然无法坐在一起和和气气喝一杯共识咖啡。当我把这些解释给那儿的一个朋友时,他大为震惊:
“妈的,你为什么非要谈到这些敏感的话题呢?!喝你的咖啡就好了,有些事情你想想就好,可千万不要说出来,这样波斯尼亚才能和平!然后你想去哪儿就继续走你的路!”
这个朋友不明白,就算我坐在那里一个字也不说,事实上我还是在说话。武克·卡拉伊里奇[3]有一句至理名言:“所写即所说。”然而我并不是这个语言学家的支持者。在我这里,真正有效力的法则是“所写即所想”。根据东方一位思想家、作家的看法,那些能跟死亡和解的人是用心讲话的。
桑卡住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心医院,她手术完正在养身体,我给她带去了汤。我向她吐露再也不能回到萨拉热窝让我多悲伤。她摸不透这出乎意料的转变是从哪儿来的。她看着我,眼神里尽是疑问。她有些吃惊,就好像她在想:“他这个新的怪念头是从哪儿来的?”她清楚我很坚定,也很有条理,就像她的妈妈一样。她朝羹匙吹着气,让汤凉下来。她咽下一口,然后想让我重拾勇气:
“他们,我的埃米尔,他们不值得你这样。至于我,等我出了医院就回那儿去。我不能把我的房子留给他们,死也不能!”
她又不说话了,接着仔细打量着我,她想深入我的悲痛之中。
“可为什么,你突然变得这么伤心啊?”她问我。
其实我的母亲跟所有的母亲一样,想让我在悲伤边缘停住脚步。
“我想象着自己还能在塞塔利斯特喝一杯咖啡,跟佐兰·比兰和帕沙一起。可我明白,在那儿,再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达成共识、和和气气地一起喝咖啡了。”
说到“共识”这个词,正在喝汤的桑卡停了下来。
“要是你说共识,就还得回到政治上去。”
“这是免不了的。”
“我的天啊,埃米尔,你有时候可真会让我恼火啊!你难道就没有什么能脱离政治的吗?”
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紧紧喉咙极力控制着。
“我知道……你是想说我跟爸爸一样?”
“不,你比他还糟。”桑卡抱住我回答道。
我笑了,继续克制着眼泪,为了不让桑卡难过。
[1] 在巴尔干半岛的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生活的人。
[2] 二人合作的第一部电影,中文译名为《罗科与他的兄弟们》。
[3] 19世纪中期的塞尔维亚作家、语言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