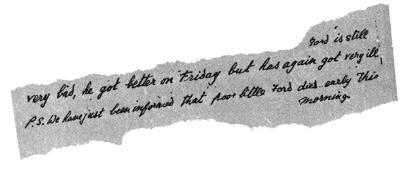女舍监
圣彼得学校的一楼全是教室,二楼是学生宿舍。宿舍这一层,那位女舍监是最高统治者,这是她的领地。这上面只有她的声音是权威声音,连十一二岁的男生都被这女魔吓坏了,因为她用一根钢棍管人。
女舍监是一个大个子女人,胸脯很大。她的岁数大概不会超过二十八岁,不过二十八岁或六十八岁又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大人就是大人,所有的大人在学校里都是危险的人物。
你只要爬到楼梯顶,把脚踏到宿舍这一层,你就在这女舍监的权力控制之下。这权力看不见的,但想到让人害怕的校长,他这会儿正潜伏在下面书房深处,女舍监只要一高兴,随时可以让你穿着睡袍下楼向这个无情的巨人汇报,这种事一发生,你就非吃藤杖不可。女舍监知道这一点,因此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
她会像闪电一样很快掠过走廊,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她的头和胸脯会忽然冲进寝室门口。“是谁扔的海绵?”那可怕的声音一下子叫起来。“是你,珀金斯,对吗?不要撒谎,珀金斯!不用申辩!我很清楚就是你干的!现在你可以穿上睡袍,到楼下去向校长汇报了!”
小珀金斯八岁半,他很慢、很不情愿地穿上睡袍和拖鞋,走过长长的走廊,走廊通到后楼梯,通向校长的私宅。我们都知道,这位女舍监会跟着他,站在楼梯口,脸上一副怪模样,然后就会听到下面很快传来藤杖的噼啪——噼啪——噼啪声。对我来说,这响声听上去总像是校长在朝他书房的天花板开枪。
现在回过头去看,毫无疑问,那女舍监实在不大喜欢小孩子。她对我们从来不笑也不说句好话,比方说软麻布粘着你膝盖上的伤口,她可不许你一点一点揭掉,她总是猛地拉,嘟囔着说:“别那么丢人现眼,婆婆妈妈的,小宝宝!”
第一学期,有一次我下楼到女舍监的房间要点碘酒涂我擦伤的膝盖,当时我还不懂进屋要敲门的规矩,我打开门就进去,她正在房间当中跟拉丁语教师维克托·科拉多先生拥抱在一起。我一进去他们两个飞快地分开,他们的脸一下子红了。

“你怎么敢不敲门就进来!”女舍监大叫,“我正要从科拉多先生的眼睛里吹掉什么东西,可你冲进来打扰了整个细致的手术!”
“我很抱歉,女舍监。”
“现在出去,五分钟后回来!”她叫道,我像颗子弹似的飞了出去。
熄灯以后,女舍监会像一只美洲豹那样在走廊里蹑手蹑脚地走,捕捉寝室门里悄悄的说话声。我们很快都知道她的听觉实在太惊人,还是不说话为妙。
有一次熄灯以后,一个叫雷格的勇敢孩子踮起脚尖走出寝室,把一些砂糖撒在走廊的地板上。雷格回来告诉我们,走廊从一头到另一头都成功地撒满了砂糖,我激动得都发抖了。我在黑暗中躺在床上等啊等,等女舍监又来暗中巡查,可是没有事情发生。我心里想,也许她正在她的房间里又给维克托·科拉多先生的眼睛取出另一粒沙尘吧。
可是忽然之间,从走廊那一头传来很响的嘎吱嘎吱声,听上去像一个巨人走在很松的小石子路上。
接着我们听到远处女舍监生气的尖叫声。“这是谁干的?”她在哇哇叫,“你们怎么敢这样做!”她嘎吱嘎吱地顺着走廊走,打开所有寝室的门,扭亮所有的灯。她的生气程度是吓人的。“出来!”她在走廊上嘎吱嘎吱地走过来走过去,大声喊叫,“自己招了吧!我要那撒糖的臭小鬼的名字!马上招!走出来!自己认罪!”
“不要招,”我们悄悄对雷格说,“我们不会把你说出去!”
雷格不吭声,他一旦招了,注定要受可怕的责罚,血淋淋的。
很快校长就从楼下被请上楼。女舍监鼻子冒烟,向他大叫救命。现在全校学生都被赶到长走廊里,我们只穿着睡衣,光着脚,站在那里都冻僵了。罪犯或者罪犯们被命令上前。
可没有人上前。
我看得出来,校长实在非常生气。他气得满脸通红,说话时唾沫四溅。
“很好!”他打雷般地叫道,“你们每个人马上把钥匙拿出来!交给舍监,她给你们保存到学期结束!所有从家里寄来的包裹从现在起将被没收!我不能容忍这种行为!”
我们把钥匙都交出去,这个学期余下来的六个星期我们很饿,可这六个星期大家也挨过去了。阿克尔继续把虫子扔进食品盒盖上的窟窿喂他的青蛙。他还用旧茶壶每天把水倒进那个窟窿,让青蛙湿湿的,过得快活。我对阿克尔把他的青蛙保养得那么好感到很佩服。他自己虽然饿肚子,可他不让他的青蛙饿肚子。从此以后,我尽力好好地对小动物。
每个寝室大约有二十张床,都是些狭窄的小床,排在两边墙旁边。寝室当中放着脸盆,我们在那里洗手洗脸刷牙,用的都是凉水,一壶壶地放在地上。你一进寝室,就不能再出去,除非你上女舍监的房间去报告,说你生病了或者受伤了。每张床底下有一个白色的夜壶,你上床之前要蹲在地板上小便干净。每当熄灯之前,整个寝室都是男生们对着夜壶小便的咚咚声。一小便完就上床,天亮前不许再起来。我相信走廊的什么地方有一个厕所,可是要上那里去只能是突然拉肚子。上这楼上的厕所就是拉肚子,那么,女舍监会马上逼着你咽下一种稠稠的白药水。这会让你便秘一个星期。
在圣彼得学校第一个悲惨的想家之夜,我蜷缩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只想着我们的房子,我的妈妈和我的姐妹。我问自己,她们在哪里呢?兰达夫在哪个方向呢?我开始要把它想出来,这也不难,因为有布里斯托尔运河帮我的忙。只要从寝室窗口望去就能看到运河,大城市加的夫和它旁边的兰达夫几乎就在河对面,只稍微往北一点。因此,只要我朝窗口转过去,我就能面对我的家。我在床上翻过身来,面朝着我的家和我的家人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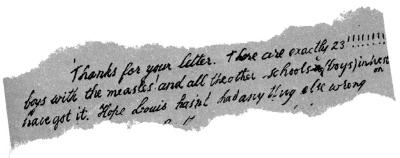
从此以后,我在圣彼得学校睡觉从来不背对我的家人。在不同的寝室和不同的床上,我要重新判断方向,布里斯托尔运河总是我的坐标,我也总是能在我的床和威尔士那边我的家之间画出一条想象的直线。我睡觉没有一次不朝着我的家人,这样做是一大安慰。
读第一个学期时,我们寝室里有一个男生叫特威迪,他一睡着就打呼噜。
“谁在说话?”女舍监冲进来叫道。我的床紧靠房门口,我记得我当时从枕头上抬起头来看她,看到她被走廊灯光照亮的侧影,觉得她看上去真是太可怕了。我觉得是她那巨大的胸脯吓着我了。我的眼睛盯住它看,只觉得它像个撞城槌,或者破冰船的船头,或者两枚高爆炸力的炸弹。
“快招!”她叫道,“谁在说话?”
我们默默地躺在那里。这时候张开嘴巴仰天熟睡的特威迪又打了个呼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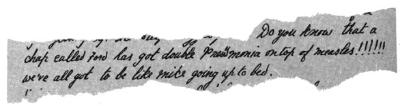
女舍监盯着特威迪看。“打呼噜是让人讨厌的坏习惯,”她说,“只有下等人才打呼噜。我们得给他一个教训。”
她没有开灯,却走进房间,随后从最近的一个脸盆里拿起一块肥皂。走廊上没灯罩的电灯用暗淡的奶油色灯光照亮了整个房间。
我们在床上全不敢坐起来,可这会儿所有的眼睛都看着女舍监,看她接下来要干什么。她总是把剪刀用一根白带子拴在她的腰间,这时,她用剪刀刮下一些肥皂片放在一只手掌上,接着她走到那倒霉的特威迪躺着的地方,很小心地把小肥皂片撒到他张开的嘴里。她有整整一把肥皂片,我想她要一直不停地撒下去了。
天啊,会发生什么事?我心里说。特威迪会呛着吗?他会窒息吗?他的喉咙会完全堵住吗?她难道要杀了他?
接着女舍监退后两步,在胸前交叉双臂,或者说在巨大的胸脯底下交叉双臂。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特威迪继续打他的呼噜。
接着他忽然开始打嗝,白色的小泡泡出现在他的嘴唇周围,泡泡越来越多,到最后,他整张脸好像都是白色的肥皂沫,看上去真吓人。接着忽然之间特威迪拼命地咳嗽和喘气,猛坐了起来,用双手抓他的脸。“噢!”他结结巴巴地说,“噢!噢!噢!噢,不!出、出、出、出什么事了?我脸上都是、是、是什么?救命啊!”
女舍监扔给他一块毛布,说:“擦干净,特威迪。别让我再听到你打呼噜。没有人教过你不要朝天睡吗?”
她说完就大踏步走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